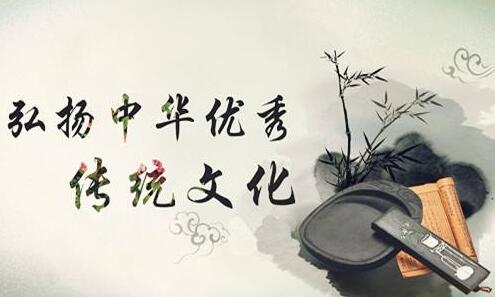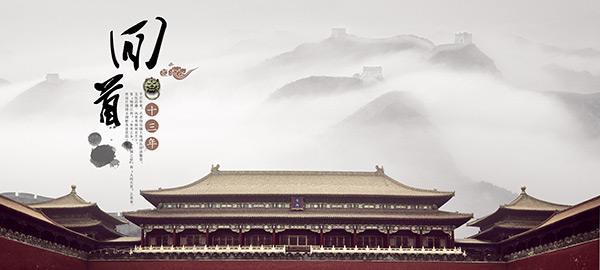冬至其实也是这样,过去结绳记事,结到顶了,就是终年。“冬”旁边加上一个偏旁,就成“终”了。就是结绳记事到年尾,到终了。底下的两点是什么呢?是冰纹碎裂的声音。北方有个说法形容冷,叫嘎嘎地冷,其实就是冰纹碎裂的声音。所以到了这个时节你还不藏吗?这时人就要睡得早点,起得晚点,要炖点补的东西。
在过去中国人养生,是春天吃芽、夏天吃叶、秋天吃果、冬天吃根。什么叫“冬吃萝卜夏吃姜”?因为这个时候根茎类的植物白薯最甜,土豆最面,萝卜最脆。我在做“汉字英雄”的评委时,有一道题是问小朋友,什么东西是地里长出来的?我们希望他们写出来的是稻子、黍子、麦子等。有个小男孩直接写道:大饼。我真的挺心疼这些孩子的,因为他们看到的饺子、面条、馄饨、包子、大饼、馒头全是从超市买的,更别说这个加工的过程了,家里都不怎么做,这就是我们的都市生活。去年大家曾讨论过烟台大学的大学生剩菜,一桌子一桌子地剩,七个保安联合起来每天就吃剩饭,最后这件事上了新闻联播了。我虽然是长在城市里,但我们小时候,70年代的时候学工学农,我们还真是住在农村,还知道怎么用镰刀,我们小的时候起码还真知道什么叫“谁知盘中餐,粒粒皆辛苦”,但到了我的学生,我的孩子真的就没有这些课了。
所以我在想农耕文化我们守住了什么?我们还真的知道“风雨四时”是什么吗?西方的记者曾经问过我:“我们也过年节,你们也过节,能不能说一下东西方这个‘节’最大的区别是什么?”我说:“简单说,你们的‘节’都是从天堂下来的,我们的‘节’都是从地里长出来的。这就是它们的不同点。”西方人过的是圣诞节、感恩节、复活节,都跟神有关。一个个体向天空、向神灵的致敬与膜拜就是他们的节。而中国人的节是什么?我们过的好多节其实都是节气。比如说清明是什么?一方面它肯定是一个节气,种瓜种豆不能误农时;另一方面它肯定是一个节日,所以风清景明之时,节气和节日是融而为一的,只有中国才有这种现象。当一个人的心真正认同四时之序,其实就有一种情怀孕育而成。我们今天缺少一种神圣的理性精神,其实也缺少这样一种感性的情怀的孕育。所以这是四时的节序。四时的节序里面也含着我们对于农耕土地最深沉的尊敬。为什么节奏都是从地里出来的?为什么中国人都过春节?以前过春节是从腊月二十三祭灶过小年就开始了,轰轰烈烈,一直到十五元宵猜了灯谜,上元节出去过完大年才结束。为什么要拿出二十几天来过这个节?因为这是冬天的节奏,到了冬藏的时候,秋天打下来的粮食才能算出有多少余粮,有了余粮才能酿得了酒。中国原来喝的酒都是粮食酒,所以要提前计算好了。所以我说我们的土地,按照中国的道理,合就合得很准,合得还有诗情画意。
中国人的这种因景而生情与四时有紧密的关系。四时风物的变化,我们今天还能说出像郭熙《林泉高致·山水训》“春山澹冶而如笑,夏山苍翠而如滴,秋山明净而如妆,冬山惨淡而如睡”的话吗?你能感觉春天的山峦都在微笑吗?这一簇一簇桃红柳绿的花开,那不就是春天的表情吗?夏山如露,露气也漂亮,蓊蓊郁郁、满眼翠绿,那种蓬勃就像遏制不住的露气一样,喷薄而升。秋山如妆,那些斑斓的颜色,跌宕成一山的妆容,那是何等的一种艳妆美人的容仪。冬天万物凋零,冬山如睡,这座山川睡去了,睡着睡着还会在梦中绽开来年新春的第一缕笑容。所以中国人跟山往往有“我见青山多妩媚,料青山,见我应如是”的情感,人跟山川是可以相看两不厌的。但是我们现在没了那个时光,也没有那个心境,这就是丢了四时啊!所以四时的情与景是怎么出来的?其实是先把自己融合进去。
第四个,与鬼神合其吉凶,这也许是最容易产生歧义的。今天这么唯物,哪儿有鬼神呢?这太容易解释了,一句话说就是我们别自己作(zuō),遭天谴。人到什么时候敬畏之心也不能丢。不是说掌握高科技了就可以狂妄无边。三尺之上有神灵,这是老百姓说的。中国人怎么看“天”?西方人也曾问过我。我说,我们没有宗教,我们不上教堂,所以我们的道德水准能够保持很稳定!他说,你们中国最可怕的就是没信仰,你们信什么?我说,我们有基本的伦理信仰。他说,伦理有那么强大吗?能替代宗教吗?我说,咱俩不小心都绊了个跟头,你怎么本能地喊:“oh,my god!”我怎么就本能地喊:“我的妈呀!”你想想约定俗成可是有最大的力量,喊神的人是因为从小就去找神,中国人遇事就喊两样:妈呀,天呀!喊妈说明你信伦理,喊天说明你信天理。天理和伦理就是我们这个民族所受的这个“礼”的底线。
但大家看看最近的这几年,都市里的恶性事件,不在于数量上频发到多少,而在于性质上不断地在挑战我们的底线。我们过去都认为,无论怎样,学校和医院都是安全的地方。看看去年小学里的性侵和医院里的贩卖婴儿,这样的事件都出来了,我们不能GDP越来越出新高,道德感却越来越刷底线。底线到底在哪儿?我还是要说中国的农村,人是不敢这么肆无忌惮的,因为有宗庙祠堂在。而现在在城市里这一切都没有。那城里人就敢不跟鬼神合吉凶吗?新闻上说一个人能有370多套房,也就是他一天住一套,整整一年还没有住完自己的家呢,要这么作,难道不遭天谴吗?中国的汉字写得特别有意思。“贪婪”这个词,贪字从“贝”,婪字从“林”,贪的是钱财,越多越好;婪字的本意就是希望自己霸占的女人多得跟树林子似的。所以贪和婪从来都是在一起的,贪婪就已经没有鬼神的概念了。人吃五谷杂粮,都有三灾六害,但别遭天谴,还要顺顺当当、风调雨顺地过去。这是农民信的观念,现在不妨让我们回到中国人的常识。
其实有这样一个坐标我认为是我们今天真正应该去考虑的,就是能不能让我们按照中国的坐标去建立中国人的格局。我们现在讲的“儒、释、道”,儒释道的哲学怎样应用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之中?儒家教我们人跟社会的关系,道家教了我们人跟自然的关系,佛教教了我们人跟自我心灵的关系。其实这几重关系就是要我们不停地去学、去悟,最后能够在自己的身上找到一种融合坐标。所以说到底,我们建立的对这个世界的洞察、把握到底是什么?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在2011年连任宣言里给联合国的乱象最后提出的一个建议,就是引用的《老子》第八十一章最后一句话:“天之道,利而不害;圣人之道,为而不争。”
其实,我们现在有很多后工业文明的乱象,说到底就是失去了秩序,于是就有很多匪夷所思的灾难出现。而人间的这个社会还有几个人做到守住本职,有所作为,不与别人纷争?为而不争,过去我们老把它当作贬义词去说。孔子说“不在其位不谋其政”,其实这是对的。什么是为而不争?这也是自己怎么样去找到自己的坐标。我想儒释道的内容,大家都有系统地学习和分析,我只想说这一切和“一”到底是什么关系?“天得一以清,地得一以宁,神得一以灵,谷得一以盈,万物得一以生,侯王得一以为天下正。”也就是我们学过的所有知识的架构不能是一个物理组合的叠加,而应该是化合的反应,就是最后你能让它动态合一。刚才王先生说到的“知行合一”,其实也是这样。要按王守仁当年的说法,叫“知是行的主意,行是知的功夫;知是行之始,行是知之诚”。圣人只做一事,不可分为二处。也就是你知的时候已经在行了,行的时候必然已经知道了,从来都不是先知而后行。所以我们现在缺少的不是资源,而是融合。
今天这个“真·善·美”的主题,如果真的能把它在自己的工作环境里面落实到天人合一,知行合一,情景合一,真、善、美就可以找到一个修行的途径。我们现在都觉得这个东西好,但是途径在哪里?我自己理解的知行合一是什么?其实是儒释道在个人修行中的融合,这样的一种融合首先其实还是从中国的儒家开始的。儒家是教我们进入社会,在社会中你去了解什么、做什么。我到现在都还觉得“仁义礼智信”就是中国的核心价值,这些价值在不同的时代,可以根据生活的一些观念去做微调,但是它的核心价值是不会变的。为什么呢?它不仅是真理,而且它是一种可实践性的真理。
完全不了解“
中国传统文化”不一定搞不好企业,但具有“传统文化”的知识,并能够在实践中运用其智慧,那么就有可能将管理做得更好,格局更为宏大,境界更为辽阔。
企业家传统文化与经营哲学高级研修班欢迎您的加入,报名电话:17786012601(向老师)。